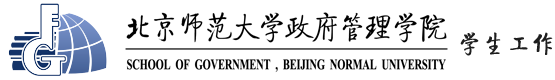学生工作
人类是唯一主动剥夺自己睡眠的物种。
——马修·沃克《我们为什么要睡觉》
手指机械性地上划屏幕,明明困得睁不开眼却还要刷完宠物博主的更新;
告诉自己“看完这集就睡”,结果从「熹妃回宫」看到「滴血验亲」;
白天啥事没干,深夜反而开始“报复性学习”,在朋友圈配文“你见过凌晨四点的校园吗”;
打完一局又开新局,这游戏怎么就停不下来呢
……
你有出现过以上这些情况吗?如果有的话,合理推测你可能患上了「睡前拖延」。顾名思义,睡前拖延是指个体在可以自由选择的情况下,习惯性地推迟其预定的就寝时间的行为。简单来说,就是你的理智和欲望会在深夜上演“宫斗剧”——白天的你保持自律理性,一到晚上却被手机迷得神魂颠倒。所以,睡前拖延也可以被称为一场蓄谋已久的“自我叛变”。

据《中国睡眠研究报告》显示,虽然有许多年轻人都认为“睡眠是每天精神充沛的来源”,但是仍有一半以上的人选择12点之后入睡。而习惯性睡前拖延带来的睡眠不足会使人们面临各种疾病风险,并且已有研究表明睡眠不足也会导致工作和学习效率的下降,对注意力和记忆力造成影响。明明「睡前拖延」会造成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为什么我们还是会选择熬夜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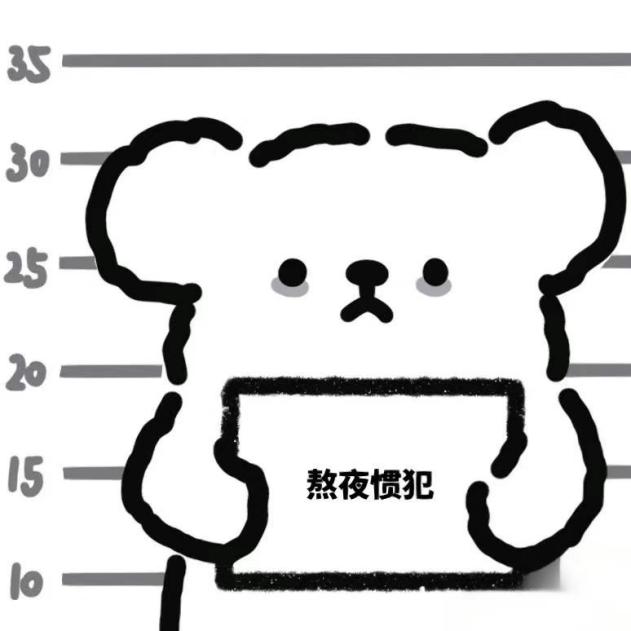
揭秘「睡前拖延」的背后逻辑
1.生理因素:夜猫族的“出厂设定”
由于每个人的生物钟存在差异,所以个体的睡眠-觉醒节律也不同。所谓睡眠-觉醒节律是指个体对睡眠与清醒时间的偏好差异,具体表现为不同的睡眠类型(早睡早起的“早鸟型” or 晚睡晚起的“夜猫型”)。此外,有研究发现,携带CRY1基因突变的人群,生物钟天生比常人晚2-4小时。所以部分人群的基因里可能早就写好了熬夜程序,自带夜猫子“出厂设置”,自然会比其他人更容易出现睡前拖延。

2.心理因素:自我控制的深夜缩水
自控力差导致自我调节失败是造成睡前拖延的重要原因。睡前拖延是一个非常容易发生在我们自我控制能力弱的状态下的问题。白天的你可能已经抵制了许多的诱惑,比如少喝一杯奶茶、少玩一把游戏。在抵制许多诱惑之后,个体的自控资源已经消耗较多,而睡觉又处在一天的结束时刻,所以睡前的我们可能没有足够的自控资源再去抵制追剧、刷短视频等娱乐活动的诱惑,从而就导致了睡前拖延。

3.社会因素:打工人的深夜狂欢
荷兰心理学家Kroese的「主动性拖延」理论指出:白天被课业/工作挤压的现代人,会将深夜视为自我补偿时段。由于白天时间被老师/老板支配,所以我们选择在晚上夺回人生控制权,并通过熬夜刷手机等方式宣告“这才是我的生活”,誓要把失去的快乐都补回来。这些活动会使人们沉浸其中而不自知,再加上电子屏幕蓝光会延迟人体分泌褪黑素的时间,导致我们的大脑处于兴奋状态,而这又进一步加强了睡前拖延。

熬夜的代价:不要以为年轻就能为所欲为!
颜值崩塌:脸上胶原蛋白的流失速度加快,而黑眼圈却成为了「面部常驻嘉宾」。
智商掉线:海马体体积显著缩小,大脑衰老加速,背个手机号仿佛马冬梅大爷附体。[海马体是大脑中负责记忆的关键区域]
情绪过山车:杏仁核活跃度激增,与想象中的「情绪稳定」越来越远,只能化身易燃易爆炸的「移动火药桶」。[杏仁核是大脑边缘系统中负责情绪加工的核心结构]

睡眠主权夺回指南
1.手机“断舍离”
对手机执行夜间流放计划,在睡前将手机和自己进行物理隔绝,比如可以将手机放在床下而不是让它跟自己一起待在床上。也可以对自己实施反向PUA,设置“再熬夜就秃头啦”的壁纸,提醒自己在睡前远离手机。针对手机屏幕投放的蓝光,则可以在日落后开启夜间模式并降低屏幕亮度,在一定程度上减低蓝光对睡眠的影响。

2.增强自控力
告诉自己“就早睡五分钟”,一点点累积,逐步增强自己对睡眠的控制力,渐变式地调整作息。也可以制作熬夜成本清单,把熬夜后果写成便签贴在床头,时刻警醒自己,反向提升自控力。此外,对自己施展社交绑架术也是个不错的方法,尝试找个早睡互促搭子,进行早睡打卡,违约的话就请对方喝奶茶。

3.设计专属“睡眠仪式”
给自己设定一个具体的睡觉时间,与“我今天要早睡”相比,规定具体的睡觉时间可能效果更好。如果你打算12点入睡的话,就可以尝试提前部署“睡眠仪式”。
22:30:完成洗漱任务,并把台灯调成暖光模式,营造睡眠氛围感。
23:00:泡脚+按摩,让身体进入“待机状态”。
23:30:放下手机,并打开纸质书阅读,文字枯燥度与你的入睡速度可能成正比哦~

治愈睡前拖延的钥匙,或许在于重新理解「清醒」与「沉睡」的共生关系——就像潮汐需要退潮之后才能再次涌起,而我们白天的高质量状态也必须从良好的睡眠开始。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可能都被动或者主动地有过睡前拖延的行为,并且这种情况在有些时候甚至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尽管如此,大家还是要照顾好自己,好好睡觉,保持健康呀~
(图片源于网络)
参考文献:
[1]李露,孙慧敏. 睡前拖延研究综述 [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20, 28 (02): 316-320.
[2]傅轶鸣,马晓涵,牟丽. 睡眠拖延行为背后的心理生理机制解析 [J]. 心理科学, 2020, 43 (05): 1190-1196.
[3]Kroese F M, De Ridder D T D, Evers C, et al. Bedtime procrastination: Introducing a new area of procrastination[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4, 5: 1-8.
[4]Horne J A, ostberg Olov.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human circadian rhythms [J]. Biological Psychology, 1977, 5(3): 179-190.
[5]Roenneberg T, Wirz- Justice A, Merrow M. Life between clocks: Daily temporal patterns of human chronotypes [J]. Journal of Biological Rhythms, 2003, 18(1): 80-90.
[6]Kroese F M, Evers C, Adriaanse M A, et al. Bedtime procrastination: A self-regulation perspective on sleep insufficiency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J].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2014, 21 (5): 853-862.

图文编辑:王宇君
图文审核:刘丹青
来源:政府管理学院学生社区化建设平台
政府管理学院生活指导室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师政管
北师政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