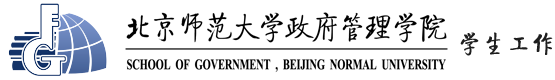学生工作
时间的异化带来的是人性的荒野,在一个由速度号令集结起来的世界,没有谁是胜利者。
——廉思《时间的暴政》
学习软件的“数据暴政”,从专注学习到被 APP 支配
考研人的“年龄焦虑”,22岁必须上岸的时间枷锁
倍速追剧的悖论,陷入“越追求效率越空虚”的循环
在效率至上的现代社会,我们对时间的追逐从未停歇——手机里装满倒计时APP,日历被色块分割成精确的时间格子,“时间管理”逐渐成为人人追捧的成功学密码。但当被“Deadline焦虑”“碎片化信息吞噬”“社会时钟规训”等情绪笼罩时,我们或许正困在一场心理漩涡:时间异化。
马克思在异化劳动理论中指出,当劳动产品、劳动过程与劳动者产生割裂时,人会失去对自身的掌控感。时间异化可以视为这一理论在当代的延伸:当时间从服务于人类发展的工具,异化为衡量价值的唯一尺度,制造焦虑的标准化模具,甚至成为支配个体存在的异己力量时,人就陷入了与时间的割裂状态。时间异化在本质上是一种人被剥离了人之本质的异化状态,并且这种异化状态也会愈发地加深对人的生活的宰制。

时间异化的表现
1.被效率工具“绑架”:越自律,越焦虑?
当番茄钟、四象限法等时间管理工具从辅助生活的手段异化为生存必需品时,时间就由客体异化为可以操纵人的主体,也导致人们掉入了“工具理性”的陷阱。
在“技术沉溺”长期的隐蔽统治下,我们变得越来越依赖于智能系统,执着于使用每日专注时长、时间利用率等与时间产出效率有关的数据来衡量自我价值,而当这些数据不达标时就会产生焦虑。与此同时,我们依赖于待办清单带来的掌控感,通过不断添加或划掉任务来获得即时快感,但却容易忽视任务本身的意义。这些对于时间效率过度追求的行为,最终会导致目标迷失,也就是使我们忘记了自己「为什么而忙碌」,进而卷入“越自律越焦虑”的怪圈。

2.时间碎片化:注意力的解构危机
在数字化时代,各种信息充斥在我们周围,时间异化正以碎片化的形态悄然蔓延。早上睁眼先刷半小时短视频,上课间隙反复刷新社交软件,写作业时每隔5分钟看一次消息……我们用“碎片化时间”填满每一个缝隙,看似高效利用时间,实际上却让完整的学习时间被切割成零散片段,而那些能让人全身心投入的“心流体验”变得越来越罕见。所以,当无数无意义的碎片占据时间的各个角落,我们在回顾一天时就常常会产生“时间消失感”——「我怎么什么事情都没做,一天就过去了呢」。

3.倒计时进行中:社会时钟的隐性控制
“22岁毕业即考研考公”“25岁前必须升职”“30岁前要买房结婚”……这些无形的时间表正在以“倒计时”的形式悄悄规训着我们,驱使着我们不断地“竞速”奔跑,把“快速”“趁早”等观念深深地植入了大脑。
一方面,我们对年龄增长充满焦虑,看到同龄人提前完成人生任务,会忍不住怀疑自己是不是落后了,哪怕内心其实并不认同这些标准;另一方面,95后创业成功、毕业前发表SCI、自律人群高能量的一天等社交媒体上的“完美时间叙事”强化了时间稀缺感,使我们掉入比较陷阱,仿佛自己的时间永远不够用。最终可能会产生内在割裂,即为了“合群”熬夜社交、为了符合“自律人设”强迫早起,明明身心俱疲,却不敢停下,只能被外部标准绑架。

我们如何一步步失去时间主权?
1.当时间变为“可以计算的货币”
现代社会习惯用“效率”“产出”衡量时间:学生按“学习时长”论努力,打工人按“工作时长”算价值,连休息都要讲求“性价比”,于是如何在更短的时间内获得更高的效率成为惯性思维。当“卷绩点”“卷实习”“卷证书”成为常态,时间就被异化为了竞争筹码。这导致我们在工作、学习、社交中追求效率,甚至将这种追求渗透到闲暇时间。我们希望在有限的闲暇时间里获得更多的享受,于是会在追剧时选择倍速播放、在旅游时将行程安排的满满当当。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需要自己的时间是有产出的。

2.数字技术的“时间殖民”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使我们与世界的联结更加方便,可以突破时空限制与其他人建立沟通;另一方面也使生活无时无刻不被技术入侵。手机和互联网打破了时间的连续性,尤其是算法推荐不断推送“下一个内容”,让我们陷入“再刷十分钟”的无限循环;社交软件的即时通讯,让我们随时处于“待命状态”,这种碎片化的生活让大脑逐渐失去了深度思考的能力,也使完整的时间体验变得破碎。与此同时,便捷的网络信息也容易制造和扩散焦虑,那些看似通过树立快速成功案例来激励年轻人的话题,实质上是把时间作为衡量标准,无形中贩卖了时间焦虑,不仅会使我们在面对所谓的社会标准时失去自我规划的主动性,还会引发未在特定时间完成任务的焦虑感。

3.社会压力下的“时间标准化盲从”
在前现代社会,时间和空间是密切相关的,时间总是与地点相关或者由特定的自然现象来判定。但随着科技的发展,时间被标准化和虚化,导致了时间与空间的分离,再加之社会文化对“成功节奏”的单一定义,就带来了双重异化:一是个体与自然时间(如昼夜节律、四季更替)的割裂,导致生物钟紊乱、季节性抑郁等问题;二是我们默认“必须按这个节奏走”,却忽视了每个人的生理节律、成长速度并不相同。
害怕“偏离轨道”的焦虑,让我们忽略了内心真正的需求,只是机械地追赶着别人的时间表。

让时间成为生命的容器而非枷锁
马克思认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但在异化时间中,我们感受到的不是如何对自己的未来负责、如何保障自己的健康或是维护自身利益,反而是将一切视为“应该”——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一种“奋斗者的荣耀”、一份“本不该获得的恩赐”,仿佛超强度工作、持续加班都是我们修来的福气。但是这福气我们真的想要吗?

当然,在现代社会中,我们既没有办法不使用手机等电子产品,也不可能让自己生活在真空状态中而不受社会的影响。所以,当我们被效率至上绑架、被社会时钟驱赶、被数据焦虑裹挟时,不妨停下脚步,问问自己:
我真正想在这段时间里成为什么样的人?
哪些事情,多年后回忆起来会让我觉得“这段时间值得”?
下次当焦虑的倒计时在心中响起时,试着闭上眼睛,感受呼吸的起伏,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比起追赶时间,更重要的是,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让每分每秒都成为生命的馈赠,而不是沉重的枷锁。

(图片源于网络)
参考文献:
[1]廉思. 时间的暴政——移动互联时代青年劳动审视 [J]. 中国青年研究, 2021, (07): 29-37+14.
[2]王杰,来昕. 倍速播放:青年闲暇时间的消费与异化 [J]. 当代青年研究, 2022, (04): 36-42.
[3]李洁,李伟. 数字异化视域下青年的时间焦虑及其破解路径 [J]. 思想理论教育, 2023, (11): 92-98.

图文编辑:王宇君
图文审核:刘丹青
来源:政府管理学院学生社区化建设平台
政府管理学院生活指导室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师政管
北师政管